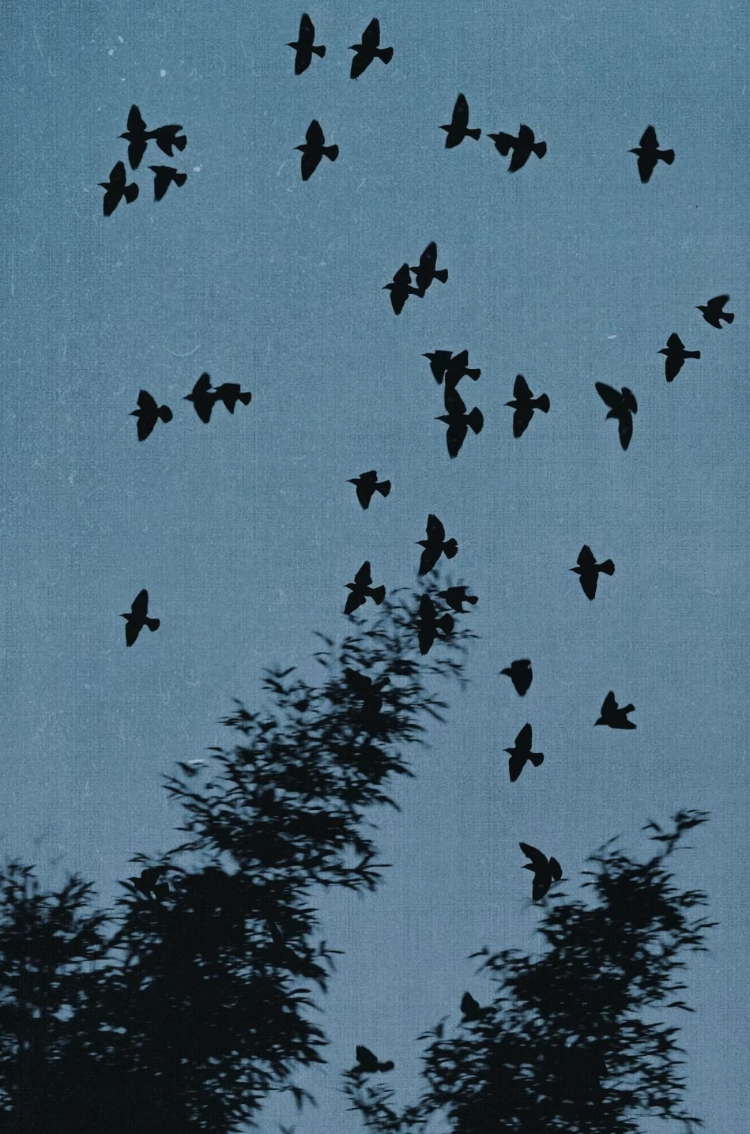最近思绪万千,总在想一些有的没的。 总想到: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。最近一些朋友们各自有各自的烦恼,朋友a家患了重度抑郁和焦虑;朋友b在烦恼要不要和伴侣讨论女性主义;朋友c工作繁忙,压力很大,每隔一小段时间周围就有同事跳槽;朋友d和前任分手了;朋友e在考虑考研的事。而我,我也有我的烦恼。 我的烦恼在于人究竟是否能摆脱傲慢、自大和偏见? 请允许我从辩论讲起。曾经有段时间对辩论感兴趣,后来在了解中对辩论失去了兴趣,就如庄子言,“道恶乎隐而有真伪?言恶乎隐而有是非?道恶乎往而不存?言恶乎存而不可?道隐于小成,言隐于荣华。”即使辩赢了,又能代表什么呢?最初参与辩论是希望在辩论中靠近真理(我指的不是一方对,一方不对,辩论时双方本身就是各有道理才值得一辩的。我指的是思索更深刻,更有意义,更引人思索),后来发现,辩论很讲究术辩,赢了的人很有可能是更擅长言语,而不是更接近真理。或许有人说,理越辩越明,辩论之中也能促进思考,可辩论是喧嚣的,争执者是浮躁的,而思考需要静心。辩论只能起到点明议题引起思考的作用,而很难做到深刻。可以说,从辩论获得的见解最高高度取决于辩论双方的思索深度(虽然即便思索深刻在辩论中也未必说得出来,或者说得清楚),但和能我辩者也未必比我高明多少,如果真的某课题感兴趣,与其花费时间在辩论输赢,实际不如读些这方面的书,与更深刻的思想家对话,然后独自思考。 但辩论带给我了对语言本身的思考。 语言是有力量的,正如辩论不需要真的更靠近真理也能获胜 ,也如社交媒体对事实的歪曲引起人们争论。语言,语言是一种工具,一把武器,语言能够构建秩序:模糊抑郁的情绪如果能用语言表述,就会被正视;无人在意的困境如果能被词语定义,就会促进解决。语言相当锋利,无论是刺向他人还是解决问题。 但语言也是有局限的,主体要将内在的思想外化就必须通过符号作为介质,可思想是流动的,而符号是停顿的,能指与所指永远分离,意义在符号下延宕。很难有人能真正用语言准确传达出意所思,也很难有人能真正从语言之下读懂含义。也因此,才有了意在言外的说法。 于是我也总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听懂了人家的意思,或者别人是不是真的明白我在说什么,说交流,我们真的交流了吗? 由此再延伸,又不得不想到互联网中的交流。彼此不再熟悉,也没有了表情和肢体动作,互联网上的交流变得更加刻板。在网络上大家更容易误解彼此的意思,进行无意义的争论,这是因为人们高估了语言的效用吗?本身用语言表述出某种意思、某个思考或某种处境就十分困难,更别提如今人们更爱吸引眼球的简短内容,互联网上引人注目的都是短篇文字或视频,短短几行字、几句话怎可能详述出真正的意思?人们(或我)自以为已经领会了屏幕对面的意思,又自以为是地做出评价,给出建议。实际上,他们真的明白了吗?他们真的看懂了吗?他们是否只是在这几行字中找到了自己,然后对自己做出回应?他们究竟是在和屏幕对面的那人对话,还是在和自己对话? 有人说互联网是放大了人性的缺陷,那么退一步思考,日常的交流又何尝不是如此?一个人永远无法真正理解另一个人的处境,如果说语言是传递意义的一种介质,那么抛掉这种介质,用其他任何方式仍然都无法达到完全准确。既然我们无法互相理解,那么交流是否很大程度上只是在自说自话?我的一位朋友说,他认为交流是一件浪漫主义的事,我认可这句话。人与人之间存在绝对的隔膜,语言是对消解这层隔膜的不懈尝试,即便它永远不可能完全成功。 这个问题暂且搁置,顺着这条线继续思考,如果说我明明知道人与人是无法真正互相理解的,每个人都有其复杂独特的人生处境,那么为何总是难以抑制地对他人做出评价?我总是以己度人,通过对自身的理解试图理解他人,解释他人。他人做出某某行为,我就下意识用某某原因解释,他人做出某个选择,我就下意识评价这选择的好坏。这是我太无知、太自大、太傲慢的缘故吧?总是认为我有评价他人、解释他人的能力和资格。 可我仍然不明白,理解他人和解释他人究竟有区别吗?“理解”难道不就是在自己的视角下解释他人?如果没有区别,所谓“理解”是否也是一种傲慢的想象?我说“我理解你”并非真的理解,而是“我能够在我的视角用理由解释你”,是“我认为我理解了你”,而不是“我真的和你感同身受”。 对我来说,理解和评价是密不可分的。我这里说的评价并不是说判断对错或好坏,而是一种情感倾向,当我试图理解他人,就自然而然会对他人的行为有情感倾向,而这情感倾向十分主观。我似乎无法平视他人,无法对某件事“知道了,但没什么看法”,我热衷于解释我所看到的世界,带着主观的偏见、带着有色眼镜。 当这样的视线投到我身上时,我痛恨这种自以为是的理解,我觉得这太无知、太傲慢。可我自己就无法抑制对他人的这种傲慢的视角。 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缺点,还是人本身固有的局限性。真的有人能摆脱傲慢、自大和偏见吗?还是只是因为我太无知,认为我自己有这样的缺点,于是人家都有。 如果能,时间或学识能否赋予我谦逊的能力?如果不能,我又如何面对自己? 人说智者谦和,懂得越多,视线越宽,可我不明白。在我狭隘的认知中,那些明智者是在杂乱的世界中建立了一座自身的思想大厦,而坚固的大厦代表着坚定的价值取向。可既然建立了价值取向,就必定有以它为衡量的“好”与“坏”,那么面对那些不符合自身价值取向的人或选择,又是以什么样的眼光面对呢? 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,我不知道是只有我有这样的想法,还是所有人都多少都想过一点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路要走,我们注定思索那些我们认为重要的问题,然后被这些思索塑造成为不同的人。